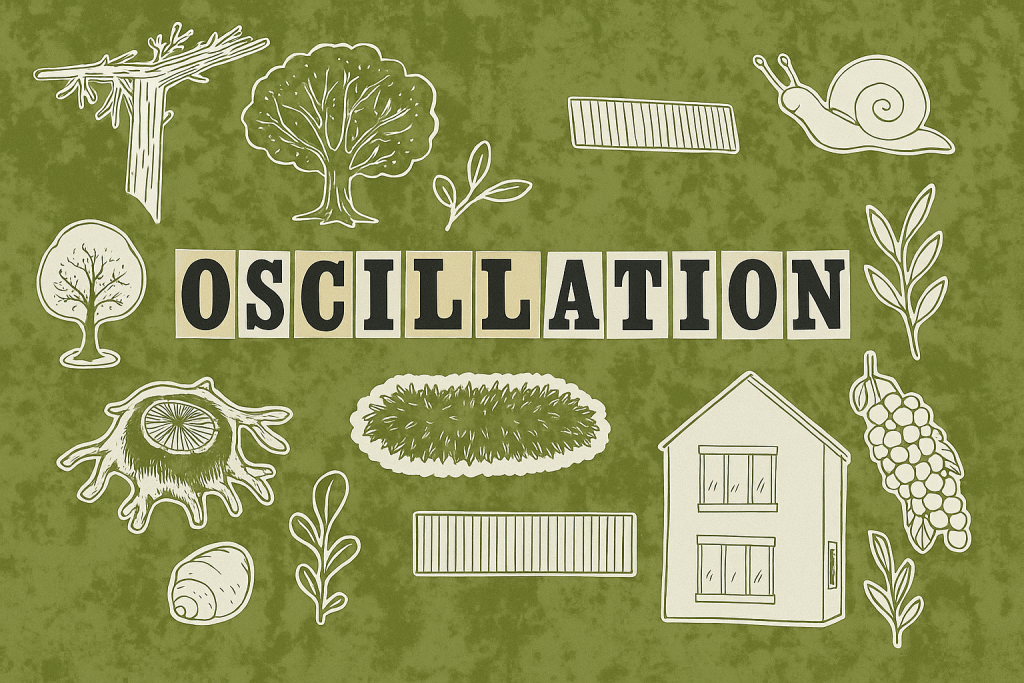
策展中的触觉与共感实践
这一期我们想围绕“材质”与“触觉”来展开叙述。于是照旧打开电脑,翻看现场采样时拍下的照片:墙面的裂纹、砖的纹理、树皮的剥落,野草,荆棘……像做设计项目一样开始整理、标注、找关键词。突然意识到在用这些熟悉的设计思维路径理解它们——“归类”“标签”“逻辑关系”。这些思维曾为我提供一种建构空间秩序的框架,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对空间活动节奏与路径的感知方式。设计思维会预设一种立场——认为材质理应被使用、被清理、被命名与被编排。这一种功能性的编排逻辑,也是一种体制性的策展语言:是可控性、清晰度与展示效率。某种意义上,这种“设计性”正是现代展陈语法的一部分:它以可预测性和视觉主导为核心,屏蔽了那些没有被定义的气味、纹理、缓慢节奏与不可读之物。

记得采样那天,我们被问道,“展览前会清理一下植物吗?”
所以,需要再次“处理”这些材质吗?当然不,这些植物、青苔、蜗牛壳、小黄花……在我们看来,它们并不是“妨碍布展”的障碍。是已经存在的故事,是我们走进去之前就已经开始“布展”的共建者。
空间合作创办人 PanPan 告诉我们,每年六月,前院总会开满黄色的小花。展览那天,说不定还会看到它们。这个院子里有自己的叙事、有自己的节奏——春天,蜗牛会爬满墙面;夏季日照变长,青苔渐渐枯萎;门口那棵树会结出像蓝莓一样的小果子,邻居家的孩子常常跑来,摘下直接放进嘴里。
这些我们无法命名、无法设计、也无意干预的东西——是我们这次策展中真正的“材质”。
它们不是布景,也不是背景,而是空间的一部分,是一种已经在发生的物质节奏,一种呼吸与腐殖的交替关系。


在以Animism(万物有灵)[1]为方法的策展框架中,我们拒绝将“材质”简化为可使用、可命名的展陈工具,而是视它们为具备感知能力与回应性的非人共建者(nonhuman co-agents)[2]。就像 Jane Bennett 在《Vibrant Matter》[3]中所言:物不是被动的,它们拥有微小的意志、情绪与生命强度。
Small Gallery 中的墙体、树皮、砖缝、土壤、湿气、声响——都不只是构成视觉场景的道具,它们正在以自己的节奏回应、干扰、塑造我们的进入方式。
策展不是为了控制观看,而是为了进入一个已有语言的生态之中,成为聆听者。
在我们的实践中,“触觉”成为进入空间的方式之一。
在不设定明确的观看路线的前提下,依据材质的组织方式、地面的纹理、墙体的变化、空气的流动,让身体自行“游走”。策展的逻辑从“组织内容”变成了“生成节奏”。这与 Sarah Pink 所强调的感官民族志类似——感知不只是经验的输入端,更是知识生成的行动过程。[4]
我们认为,“材质”不是信息的载体,而是节奏的发生器,是召唤身体感知、引导非语言经验的策展“语言”。策展团队在采样中所记录下的,不是“用于布展的材料”,而是这些材料所激发出来的感官转向与节奏反馈。


在 Oscillation 中,蜗牛壳不是“有趣的发现”,而是时间的证据;树皮不是“场地肌理”,而是生命过程的一种回响;青苔的干枯不是“表面变化”,而是空间在回应气候变化与日照节奏的一种反馈机制。
这不是一次关于材质的展示,而是一种关于“与材质共生”的策展练习。
我们不再使用材质,而是和它们一起生活;我们不再命名植物,而是在它们面前安静地驻足;我们不再布置展览,而是等待展览在这些材料之间缓慢显现。
在 Oscillation 里,策展不是一个指令性的规划,而是一种持续生成的共感。
[1]Anselm Franke, ed., Animism (Berlin: Sternberg Press, 2010).
[2] Bruno Latour, Reassembling the Social: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-Network-Theory 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5), pp. 72–75.
[3] Jane Bennett, Vibrant Matter: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(Durham, NC: Duke University Press, 2010), p. viii.
[4] Sarah Pink, Doing Sensory Ethnography, 2nd edn (London: SAGE Publications, 2015), p. 23.
发表回复